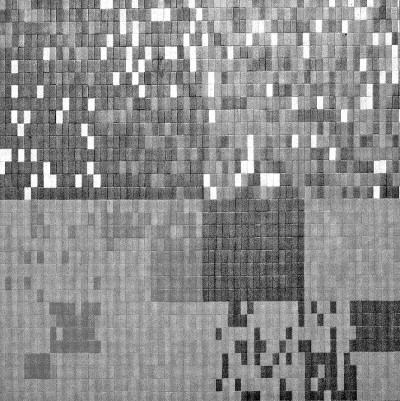 作者:焦亚男(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数字艺术从以计算机生成艺术为标志的第一代、以数字奇迹为标志的第二代、以互动艺术为标志的第三代,迭代发展到目前以人工智能艺术为标志的第四代。当我们陶醉在四代数字艺术构建的万花筒般的美学景观中时,我们不能忘记炸nack,数字艺术的火种。作为最早将数学逻辑、计算机编程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先驱者,纳克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不仅奠定了数字艺术的早期形态,也建立了数字美学大厦的基本框架。为了表彰他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国际计算机图形学信用联盟授予他“2025 Dig意大利艺术终身成就奖。”
纳克作品《生成美学i》资料图
1 成为一名跨界艺术家
纳克1938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60年在斯图加特大学学习数学,1963年在斯图加特大学计算中心实习,协助负责“程序库”的老师。他的工作性质就像助教,又有点像软件开发人员。一天早上,计算中心主任沃尔特·诺德尔告诉他,计算中心打算购买一台绘图机,但没有合适的软件,并要求纳克编写一个绘图程序。 Knodel 教授的 T 给了 rustful 委员会一个机会,为新型自动平板绘图仪 Z64 开发软件程序。正是从此开始的编程实验,开始了纳克一生中数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探索阶段。
油炸纳克文件照片
一个这一阶段,纳克的创作以“绘图仪几何美学”为中心。 1963年至1965年,他使用ER56计算机和Z64高精度绘图仪创作了“随机多边形”系列、“线簇II”系列、“随机遍历”系列和“向保罗·克利致敬”系列。 1965年11月,他与乔治·内斯在斯图加特的Wendelin Niedlich画廊举办了联合展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艺术特别展览之一。此次展出的《直线簇II》利用十字线密度的变化产生视觉深度,线条精度达到0.1毫米,成为计算机生成艺术的标志性起点。当这些算法艺术首次出现在传统艺术场所时,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业评论家都受到了极大的困惑和争论。算法革命对艺术产生了几乎未被注意到的影响。
纳克作品《直线簇No.2》资料图
1966年,纳克推出了“Through Grating”系列,利用当时的基本计算机算法语言,将拓扑中的“连接”概念转化为栅格线的参数变化。他在1967年至1968年创作的“矩阵乘法”系列,直接将数学运算转化为视觉符号。计算机自动处理的矩阵乘法的结果成为色彩和形式的来源。1968年,他的作品入选当代艺术研究所的“控制论的意外发现”展览。伦敦和萨格勒布的“Trend 4”展览。1969年,他创作了“生成美学I”系列,从1963年到1969年,他使用的编程算法不断升级,逐渐从机器语言转向PL/I语言(IBM开发的一种多用途编程语言)。
1970年后,纳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数字艺术的理论探索上。在全面总结和提炼实践的基础上他创作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数字艺术,并于1974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信息处理美学》。这部著作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算法艺术”、“生成艺术”、“什么是计算机生成艺术”等学术争议的主要问题,而且系统地发展了以“逻辑-参数变量-视觉输出”为主要结构的算法艺术机制的创作,是第一部数字艺术的方法专着,对建立数字艺术的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计算机艺术的历史地位。
进入21世纪,纳克以“经典作品的当代翻译”为主再次爆发出强烈的热情。 2004年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举办的“精准愉悦”特展中,他在互动投影设备中再现了1966年创作的经典作品《在光栅上行走》。观众的动作可以直接控制动作栏杆的改造,实现了“可视化过程”的当代升级。该设备被卡尔斯鲁厄艺术和媒体中心永久收藏。百年来,他热情拥抱NFT技术,以1960年的经典作品和其他著名画家为原型,创作了《扇面画》(2015)、《直线簇》(2018)、《向格哈德·里希特致敬》(20 18)、《向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致敬》(2018)、《彩色网格》(2025),凯特收藏苏黎世Wass画廊、德国数字艺术博物馆、英国Gazelli艺术博物馆等著名艺术机构。
60多年来,NACK以算法为纽带,将数学、创新技术和艺术自由完美融合,最终成为用代码书写视觉诗歌的数字艺术家。
2 弘扬算法艺术三大审美标志
纳克开创的数字艺术创作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他他们没有用计算机来模仿传统艺术(如油画和素描),而是热衷于获取和探索算法这一新媒介的特征,建立了数字艺术的三个主要审美身份。
一是“算法生成”和“抑制随机性”之美。这是Nak Art的主要特点。他的作品之美并不在于最终的静态图像,而在于孕育图像的“形成过程”。例如,在创作“随机多边形”系列时,他设定了多边形生成的基本规则,同时还引入了随机数来确定多边形的边数、角度和位置。那么,每个任务都是由同一组基因(算法)诞生的独特生命形式,由不同的随机数触发。这种美既不是纯粹的人为安排,也不是绝对的失控意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种受控的、意想不到的绽放之美。oms 在严格的规则框架内。这与传统艺术中依靠艺术家双手的“笔触”和“韵律”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植根于逻辑和可能性的新的审美体验。
二是“系统探索”和“顺序呈现”之美。深受数学思维的影响,纳克的创作很少是单一的“杰作”,而更像是对视觉命题的系统研究。以“矩阵乘法”系列为例,纳克以简单的矩形为基本单位,并通过编程让这些矩形在网格上有规律地旋转。他会为整个系列设定一个规则,然后通过调整参数(例如增加旋转角度),他会生成数十甚至数百件相似但不同的作品,经常并排展示。这种创作方法所带来的美就是顺序和比较。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完美作品而是形式系统内丰富的可能性和进化逻辑。这类美学强调的不是艺术的“独特性”,而是艺术背后“生成系统”的丰富性和严密性。
三是“媒体自显”与“理性朴素”之美。纳克的工作从未试图隐藏这台计算机的起源;相反,他刻意强调并赞扬这种媒介的这些品质。轮廓所描绘出的精确而冷静的线条、有限的色彩(早期多为黑白)、算法生成的人手难以准确再现的复杂几何结构,成为他作品视觉语言的一部分。观看他的画作,比如“线簇”系列中精确的直线图案,观者可以清晰地“读懂”其背后的计算过程和机械执行的痕迹。这类美学不追求情感宣泄,不追求叙事性。叙事,却呈现出一种平静、清晰、高度理性的质朴之美。它引导观众思考艺术品的本质:当艺术家的双手被代码取代时,艺术的灵魂更集中在其立意的严谨与逻辑之美?这种创作理念与传统抽象艺术,如蒙德里安的“构图”有着根本的区别。蒙德里安的几何构图依赖于手工绘制,线条排列的准确性和规律性受到人力的限制。但直线Nack线是由程序控制的,线距误差不超过0.1毫米。这种机械精度是传统手工绘画无法达到的。
通过这三个独特的美学标志,NACK成功地将数字艺术从一种新颖的技术表现形式提升为一种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审美价值的独立艺术形式。正如他所强调的,“算法本身就是艺术,是一种艺术”乌蒂。”
3 定义独特的艺术家主张
纳克的数字艺术作品不仅在美学上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而且在主题表达上也独一无二。其主题之一是“让无形的信息和系统变得可见”。 Nak 本质上是信息结构的视觉翻译器。他热衷于将抽象概念、逻辑关系和数学结构转化为可见的图形,这与传统艺术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情感具体为主要命题,如伦勃朗的《夜巡》传达英雄主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控诉战争的残酷……艺术家利用具体的场景或符号,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可理解的视觉。纳克的作品致力于数学概念的纪念,将微分、概率等抽象的数理逻辑转化为直观的图形语言,让观众欣赏到数学之美无需专业知识。 1965年的《向保罗·克利致敬》就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瑞士著名画家保罗·克利认为“线是行走的点”。他认为线条是独立且富有表现力的元素。线条抽象又具体,能创造出丰富的韵律。 NACK用数学逻辑重构了这个概念,用程序让线条按照预设的概率规则“行走”。作品中,线条的角度角度和延伸长度是在数学约束下由随机函数生成的,既保持了“行走”的自由感,又隐藏了概率分布的数学规律。从线条蜿蜒的轨迹中,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随机中的秩序”这个抽象的数学概念——线条看似随机的运动,实际上每一步都遵循着程序设定的概率模型,实现了精确的配合。数学逻辑和视觉表达之间的联系。这种用图形读懂数学的方式是传统艺术所望尘莫及的。数字技术的可编程性使抽象的公式成为有形的视觉秩序。因此,纳克艺术的主题首先是关于“理解”,关于我们如何以结构化的审美方式来理解世界,以及这种理解如何体现在世界独特的审美形式之间。
纳克作品《向保罗·克利致敬》档案照片
保罗·克利的《红气球》档案照片
纳克艺术作品的另一个艺术哲学命题是规则与偶然性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对主要矛盾:一方面,有预设的、严格的算法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存在着预设的、严格的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随机函数的引入代表着混乱和不确定性。 1965年创作的《随机多边形》是联合国无疑是一部深刻揭示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作品由一条连续的折线组成,NACK在程序中设置了双重逻辑:一方面用严格的代码限制折线的方向范围(仅限水平、特定倾斜角度和偏差方向),生成规则的技术框架;另一方面,引入随机函数来确定顶点坐标,模拟人类创造的自由和灵性。最终的多边形不仅表现出程序提供的规则几何形状,而且由于随机参数而表现出手工创作的独特性。没有两件作品具有完全相同的多边形轨迹。纳克的艺术展现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他通过自己的艺术技巧向世人证明,最具活力的创作往往并非来自于完全的控制或完全的自由,而是诞生于规则与偶然之间的博弈边缘。赛。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为理解自然规律、社会进化乃至人工智能的创造力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此外,纳克的作品还积极触及“人机协同创作”的AI艺术创作主题。在纳克的创作模型中,艺术家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对抗的。艺术家负责定义问题的边界和创作的基本规则(即设计算法),而计算机则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在这个规则空间内进行大规模、高速的探索和生成。人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态度、审美判断和设计规则上,机器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执行力和推理能力上。 1999年NACK主办的“Compart:计算机艺术空间”项目中设计的互动装置就是一个实际例子这个主题。 NACK及其团队开发的参数交互系统允许观看者通过触摸屏调整线条移动的密度、角度和速度,从而实时生成动态图形。当观众在屏幕上滑动改变线变化频率参数时,图像会逐渐从稀疏的线变成密集的视觉矩阵;当调整随机偏差值时,规则的几何数字就会呈现智能变化。这一装置打破了艺术创作者传统的单向输出模式。听众既是创作过程的欣赏者,也是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不同的观众由于习惯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系统同时显示的参数变化让观众直观地了解操作-参数-图形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人机交互和协作的模型明确地预设了这就是6??0年前我们今天在AIGC领域热议的“人机诗人”范式。
4.奠定数字美学的理论基础
NACK不仅是数字艺术的成功实践者,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理论家。他是“信息美学”的主要创始人。该理论试图利用信息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工具对审美现象进行定量和结构化的分析。其领导力表现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纳克的信息美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基本假设——审美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过程。在他看来,算法艺术品就是包含一定“信息结构”的东西。观众欣赏作品的过程就是接受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审美体验或美的强度与审美体验密切相关。作品所传递的信息的结构。借鉴信息论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的信息结构往往处于完全有序(“冗余”太高,导致乏味)和完全无序(“熵”太高,导致误解)之间的最佳平衡。例如,在他的“矩阵乘法”系列作品中,有序网格是高度的“冗余”,提供了顺序;而矩形旋转的随机变化引入了“熵”,带来了新鲜感和动感。两者的平衡有助于提高作品的美感。这一理论尝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视角,可以对高度主观的“美”感进行测试和建模。
其次,这一理论具有浓厚的“反浪漫”色彩,主张基于计算的“理性美学”。这与传统审美形成鲜明对比不要强调天才、灵感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信息美学并不主要关注“艺术表达什么”(内容),而是关注“艺术如何构建其形式”(结构)。它是关于艺术创作作为一种基于逻辑规则的建构活动形式。纳克有时会批评计算机艺术仅被视为技术奇迹的观点。他强调,这个核心的真正价值在于艺术家设计的算法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和逻辑之美。这促使人们思考,艺术的价值是否部分在于其观念的严密性、逻辑的自洽性、生成过程的清晰性。
而且,信息美学体现了数字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过程”本质。对于油画来说,画布上的作品是完成的、封闭的东西。但在Nack的信息美学视野下,alg的真正核心基于算法的艺术是生成作品的“过程”,即算法程序。最终图像只是该过程在某个时刻的示例或输出。这意味着数字艺术品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潜在的系统,包含无限数量的可能的视觉实现。这种“过程胜于结果”的观点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的概念,并直接观察和影响了随后软件艺术、生成艺术、交互艺术的蓬勃发展。
最终,纳克的信息美学理论打破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为数字艺术建立了独立的美学体系。 1960年,当数字艺术首次出现时,艺术界通常使用传统的审美标准,例如形状的均匀性、色彩的和谐性和笔触的活力来评价数字作品。因此,数字艺术一直被认为是边缘艺术。有些人认为机器生成器过时的图形缺乏情感,不被视为艺术,而其他人则将其归类为设计而不是纯粹的艺术。纳克敏锐地意识到数字艺术需要有自己的审美体系,否则就无法摆脱传统艺术的阴影。因此,他从数学和信息论出发,提出以“信息密度”取代传统艺术美学中的“再现的准确性”,作为数字艺术的主要审美标准。他认为数字艺术的本质是基于程序的生成而不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其审美标准应该是“信息密度”,即“作品中包含的重要逻辑信息的组织数量和效率”。这个标准彻底摧毁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他明确指出,数字艺术不需要追求“像传统艺术一样”,其审美价值在于“逻辑信息的丰富性和组织性”。信息”。
从1963年的处女作《随机多边形》到2025年的NFT新作《多彩网格》,纳克始终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不断探索和培育几何之美、生成之美、理性之美的新世界。今天,当我们徜徉在人工智能艺术的奇妙世界,体验“人人都是全能艺术家”的创作乐趣时,我们一定要记住纳克的名言:数字美学的本质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利用新的工具探索人类表达的边界,用逻辑和美来传达对世界的思考。数字艺术的未来不在于技术能走多远,而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技术来表达对人类、对生命、对世界的关注。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0日第13页)
作者:焦亚男(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数字艺术从以计算机生成艺术为标志的第一代、以数字奇迹为标志的第二代、以互动艺术为标志的第三代,迭代发展到目前以人工智能艺术为标志的第四代。当我们陶醉在四代数字艺术构建的万花筒般的美学景观中时,我们不能忘记炸nack,数字艺术的火种。作为最早将数学逻辑、计算机编程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先驱者,纳克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不仅奠定了数字艺术的早期形态,也建立了数字美学大厦的基本框架。为了表彰他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国际计算机图形学信用联盟授予他“2025 Dig意大利艺术终身成就奖。”
纳克作品《生成美学i》资料图
1 成为一名跨界艺术家
纳克1938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60年在斯图加特大学学习数学,1963年在斯图加特大学计算中心实习,协助负责“程序库”的老师。他的工作性质就像助教,又有点像软件开发人员。一天早上,计算中心主任沃尔特·诺德尔告诉他,计算中心打算购买一台绘图机,但没有合适的软件,并要求纳克编写一个绘图程序。 Knodel 教授的 T 给了 rustful 委员会一个机会,为新型自动平板绘图仪 Z64 开发软件程序。正是从此开始的编程实验,开始了纳克一生中数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探索阶段。
油炸纳克文件照片
一个这一阶段,纳克的创作以“绘图仪几何美学”为中心。 1963年至1965年,他使用ER56计算机和Z64高精度绘图仪创作了“随机多边形”系列、“线簇II”系列、“随机遍历”系列和“向保罗·克利致敬”系列。 1965年11月,他与乔治·内斯在斯图加特的Wendelin Niedlich画廊举办了联合展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艺术特别展览之一。此次展出的《直线簇II》利用十字线密度的变化产生视觉深度,线条精度达到0.1毫米,成为计算机生成艺术的标志性起点。当这些算法艺术首次出现在传统艺术场所时,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业评论家都受到了极大的困惑和争论。算法革命对艺术产生了几乎未被注意到的影响。
纳克作品《直线簇No.2》资料图
1966年,纳克推出了“Through Grating”系列,利用当时的基本计算机算法语言,将拓扑中的“连接”概念转化为栅格线的参数变化。他在1967年至1968年创作的“矩阵乘法”系列,直接将数学运算转化为视觉符号。计算机自动处理的矩阵乘法的结果成为色彩和形式的来源。1968年,他的作品入选当代艺术研究所的“控制论的意外发现”展览。伦敦和萨格勒布的“Trend 4”展览。1969年,他创作了“生成美学I”系列,从1963年到1969年,他使用的编程算法不断升级,逐渐从机器语言转向PL/I语言(IBM开发的一种多用途编程语言)。
1970年后,纳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数字艺术的理论探索上。在全面总结和提炼实践的基础上他创作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数字艺术,并于1974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信息处理美学》。这部著作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算法艺术”、“生成艺术”、“什么是计算机生成艺术”等学术争议的主要问题,而且系统地发展了以“逻辑-参数变量-视觉输出”为主要结构的算法艺术机制的创作,是第一部数字艺术的方法专着,对建立数字艺术的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计算机艺术的历史地位。
进入21世纪,纳克以“经典作品的当代翻译”为主再次爆发出强烈的热情。 2004年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举办的“精准愉悦”特展中,他在互动投影设备中再现了1966年创作的经典作品《在光栅上行走》。观众的动作可以直接控制动作栏杆的改造,实现了“可视化过程”的当代升级。该设备被卡尔斯鲁厄艺术和媒体中心永久收藏。百年来,他热情拥抱NFT技术,以1960年的经典作品和其他著名画家为原型,创作了《扇面画》(2015)、《直线簇》(2018)、《向格哈德·里希特致敬》(20 18)、《向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致敬》(2018)、《彩色网格》(2025),凯特收藏苏黎世Wass画廊、德国数字艺术博物馆、英国Gazelli艺术博物馆等著名艺术机构。
60多年来,NACK以算法为纽带,将数学、创新技术和艺术自由完美融合,最终成为用代码书写视觉诗歌的数字艺术家。
2 弘扬算法艺术三大审美标志
纳克开创的数字艺术创作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他他们没有用计算机来模仿传统艺术(如油画和素描),而是热衷于获取和探索算法这一新媒介的特征,建立了数字艺术的三个主要审美身份。
一是“算法生成”和“抑制随机性”之美。这是Nak Art的主要特点。他的作品之美并不在于最终的静态图像,而在于孕育图像的“形成过程”。例如,在创作“随机多边形”系列时,他设定了多边形生成的基本规则,同时还引入了随机数来确定多边形的边数、角度和位置。那么,每个任务都是由同一组基因(算法)诞生的独特生命形式,由不同的随机数触发。这种美既不是纯粹的人为安排,也不是绝对的失控意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种受控的、意想不到的绽放之美。oms 在严格的规则框架内。这与传统艺术中依靠艺术家双手的“笔触”和“韵律”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植根于逻辑和可能性的新的审美体验。
二是“系统探索”和“顺序呈现”之美。深受数学思维的影响,纳克的创作很少是单一的“杰作”,而更像是对视觉命题的系统研究。以“矩阵乘法”系列为例,纳克以简单的矩形为基本单位,并通过编程让这些矩形在网格上有规律地旋转。他会为整个系列设定一个规则,然后通过调整参数(例如增加旋转角度),他会生成数十甚至数百件相似但不同的作品,经常并排展示。这种创作方法所带来的美就是顺序和比较。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完美作品而是形式系统内丰富的可能性和进化逻辑。这类美学强调的不是艺术的“独特性”,而是艺术背后“生成系统”的丰富性和严密性。
三是“媒体自显”与“理性朴素”之美。纳克的工作从未试图隐藏这台计算机的起源;相反,他刻意强调并赞扬这种媒介的这些品质。轮廓所描绘出的精确而冷静的线条、有限的色彩(早期多为黑白)、算法生成的人手难以准确再现的复杂几何结构,成为他作品视觉语言的一部分。观看他的画作,比如“线簇”系列中精确的直线图案,观者可以清晰地“读懂”其背后的计算过程和机械执行的痕迹。这类美学不追求情感宣泄,不追求叙事性。叙事,却呈现出一种平静、清晰、高度理性的质朴之美。它引导观众思考艺术品的本质:当艺术家的双手被代码取代时,艺术的灵魂更集中在其立意的严谨与逻辑之美?这种创作理念与传统抽象艺术,如蒙德里安的“构图”有着根本的区别。蒙德里安的几何构图依赖于手工绘制,线条排列的准确性和规律性受到人力的限制。但直线Nack线是由程序控制的,线距误差不超过0.1毫米。这种机械精度是传统手工绘画无法达到的。
通过这三个独特的美学标志,NACK成功地将数字艺术从一种新颖的技术表现形式提升为一种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审美价值的独立艺术形式。正如他所强调的,“算法本身就是艺术,是一种艺术”乌蒂。”
3 定义独特的艺术家主张
纳克的数字艺术作品不仅在美学上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而且在主题表达上也独一无二。其主题之一是“让无形的信息和系统变得可见”。 Nak 本质上是信息结构的视觉翻译器。他热衷于将抽象概念、逻辑关系和数学结构转化为可见的图形,这与传统艺术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情感具体为主要命题,如伦勃朗的《夜巡》传达英雄主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控诉战争的残酷……艺术家利用具体的场景或符号,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可理解的视觉。纳克的作品致力于数学概念的纪念,将微分、概率等抽象的数理逻辑转化为直观的图形语言,让观众欣赏到数学之美无需专业知识。 1965年的《向保罗·克利致敬》就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瑞士著名画家保罗·克利认为“线是行走的点”。他认为线条是独立且富有表现力的元素。线条抽象又具体,能创造出丰富的韵律。 NACK用数学逻辑重构了这个概念,用程序让线条按照预设的概率规则“行走”。作品中,线条的角度角度和延伸长度是在数学约束下由随机函数生成的,既保持了“行走”的自由感,又隐藏了概率分布的数学规律。从线条蜿蜒的轨迹中,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随机中的秩序”这个抽象的数学概念——线条看似随机的运动,实际上每一步都遵循着程序设定的概率模型,实现了精确的配合。数学逻辑和视觉表达之间的联系。这种用图形读懂数学的方式是传统艺术所望尘莫及的。数字技术的可编程性使抽象的公式成为有形的视觉秩序。因此,纳克艺术的主题首先是关于“理解”,关于我们如何以结构化的审美方式来理解世界,以及这种理解如何体现在世界独特的审美形式之间。
纳克作品《向保罗·克利致敬》档案照片
保罗·克利的《红气球》档案照片
纳克艺术作品的另一个艺术哲学命题是规则与偶然性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对主要矛盾:一方面,有预设的、严格的算法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存在着预设的、严格的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随机函数的引入代表着混乱和不确定性。 1965年创作的《随机多边形》是联合国无疑是一部深刻揭示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作品由一条连续的折线组成,NACK在程序中设置了双重逻辑:一方面用严格的代码限制折线的方向范围(仅限水平、特定倾斜角度和偏差方向),生成规则的技术框架;另一方面,引入随机函数来确定顶点坐标,模拟人类创造的自由和灵性。最终的多边形不仅表现出程序提供的规则几何形状,而且由于随机参数而表现出手工创作的独特性。没有两件作品具有完全相同的多边形轨迹。纳克的艺术展现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他通过自己的艺术技巧向世人证明,最具活力的创作往往并非来自于完全的控制或完全的自由,而是诞生于规则与偶然之间的博弈边缘。赛。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为理解自然规律、社会进化乃至人工智能的创造力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此外,纳克的作品还积极触及“人机协同创作”的AI艺术创作主题。在纳克的创作模型中,艺术家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对抗的。艺术家负责定义问题的边界和创作的基本规则(即设计算法),而计算机则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在这个规则空间内进行大规模、高速的探索和生成。人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态度、审美判断和设计规则上,机器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执行力和推理能力上。 1999年NACK主办的“Compart:计算机艺术空间”项目中设计的互动装置就是一个实际例子这个主题。 NACK及其团队开发的参数交互系统允许观看者通过触摸屏调整线条移动的密度、角度和速度,从而实时生成动态图形。当观众在屏幕上滑动改变线变化频率参数时,图像会逐渐从稀疏的线变成密集的视觉矩阵;当调整随机偏差值时,规则的几何数字就会呈现智能变化。这一装置打破了艺术创作者传统的单向输出模式。听众既是创作过程的欣赏者,也是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不同的观众由于习惯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系统同时显示的参数变化让观众直观地了解操作-参数-图形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人机交互和协作的模型明确地预设了这就是6??0年前我们今天在AIGC领域热议的“人机诗人”范式。
4.奠定数字美学的理论基础
NACK不仅是数字艺术的成功实践者,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理论家。他是“信息美学”的主要创始人。该理论试图利用信息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工具对审美现象进行定量和结构化的分析。其领导力表现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纳克的信息美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基本假设——审美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过程。在他看来,算法艺术品就是包含一定“信息结构”的东西。观众欣赏作品的过程就是接受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审美体验或美的强度与审美体验密切相关。作品所传递的信息的结构。借鉴信息论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的信息结构往往处于完全有序(“冗余”太高,导致乏味)和完全无序(“熵”太高,导致误解)之间的最佳平衡。例如,在他的“矩阵乘法”系列作品中,有序网格是高度的“冗余”,提供了顺序;而矩形旋转的随机变化引入了“熵”,带来了新鲜感和动感。两者的平衡有助于提高作品的美感。这一理论尝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视角,可以对高度主观的“美”感进行测试和建模。
其次,这一理论具有浓厚的“反浪漫”色彩,主张基于计算的“理性美学”。这与传统审美形成鲜明对比不要强调天才、灵感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信息美学并不主要关注“艺术表达什么”(内容),而是关注“艺术如何构建其形式”(结构)。它是关于艺术创作作为一种基于逻辑规则的建构活动形式。纳克有时会批评计算机艺术仅被视为技术奇迹的观点。他强调,这个核心的真正价值在于艺术家设计的算法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和逻辑之美。这促使人们思考,艺术的价值是否部分在于其观念的严密性、逻辑的自洽性、生成过程的清晰性。
而且,信息美学体现了数字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过程”本质。对于油画来说,画布上的作品是完成的、封闭的东西。但在Nack的信息美学视野下,alg的真正核心基于算法的艺术是生成作品的“过程”,即算法程序。最终图像只是该过程在某个时刻的示例或输出。这意味着数字艺术品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潜在的系统,包含无限数量的可能的视觉实现。这种“过程胜于结果”的观点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的概念,并直接观察和影响了随后软件艺术、生成艺术、交互艺术的蓬勃发展。
最终,纳克的信息美学理论打破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为数字艺术建立了独立的美学体系。 1960年,当数字艺术首次出现时,艺术界通常使用传统的审美标准,例如形状的均匀性、色彩的和谐性和笔触的活力来评价数字作品。因此,数字艺术一直被认为是边缘艺术。有些人认为机器生成器过时的图形缺乏情感,不被视为艺术,而其他人则将其归类为设计而不是纯粹的艺术。纳克敏锐地意识到数字艺术需要有自己的审美体系,否则就无法摆脱传统艺术的阴影。因此,他从数学和信息论出发,提出以“信息密度”取代传统艺术美学中的“再现的准确性”,作为数字艺术的主要审美标准。他认为数字艺术的本质是基于程序的生成而不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其审美标准应该是“信息密度”,即“作品中包含的重要逻辑信息的组织数量和效率”。这个标准彻底摧毁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他明确指出,数字艺术不需要追求“像传统艺术一样”,其审美价值在于“逻辑信息的丰富性和组织性”。信息”。
从1963年的处女作《随机多边形》到2025年的NFT新作《多彩网格》,纳克始终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不断探索和培育几何之美、生成之美、理性之美的新世界。今天,当我们徜徉在人工智能艺术的奇妙世界,体验“人人都是全能艺术家”的创作乐趣时,我们一定要记住纳克的名言:数字美学的本质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利用新的工具探索人类表达的边界,用逻辑和美来传达对世界的思考。数字艺术的未来不在于技术能走多远,而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技术来表达对人类、对生命、对世界的关注。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0日第13页)
Fried Nack:算法本身就是一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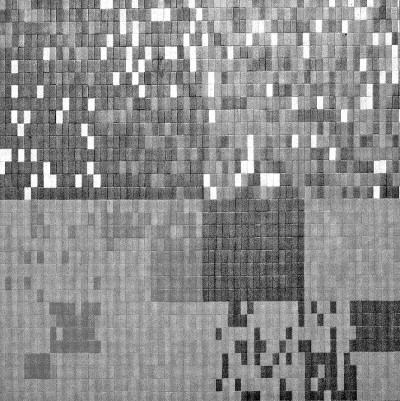 作者:焦亚男(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数字艺术从以计算机生成艺术为标志的第一代、以数字奇迹为标志的第二代、以互动艺术为标志的第三代,迭代发展到目前以人工智能艺术为标志的第四代。当我们陶醉在四代数字艺术构建的万花筒般的美学景观中时,我们不能忘记炸nack,数字艺术的火种。作为最早将数学逻辑、计算机编程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先驱者,纳克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不仅奠定了数字艺术的早期形态,也建立了数字美学大厦的基本框架。为了表彰他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国际计算机图形学信用联盟授予他“2025 Dig意大利艺术终身成就奖。”
纳克作品《生成美学i》资料图
1 成为一名跨界艺术家
纳克1938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60年在斯图加特大学学习数学,1963年在斯图加特大学计算中心实习,协助负责“程序库”的老师。他的工作性质就像助教,又有点像软件开发人员。一天早上,计算中心主任沃尔特·诺德尔告诉他,计算中心打算购买一台绘图机,但没有合适的软件,并要求纳克编写一个绘图程序。 Knodel 教授的 T 给了 rustful 委员会一个机会,为新型自动平板绘图仪 Z64 开发软件程序。正是从此开始的编程实验,开始了纳克一生中数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探索阶段。
油炸纳克文件照片
一个这一阶段,纳克的创作以“绘图仪几何美学”为中心。 1963年至1965年,他使用ER56计算机和Z64高精度绘图仪创作了“随机多边形”系列、“线簇II”系列、“随机遍历”系列和“向保罗·克利致敬”系列。 1965年11月,他与乔治·内斯在斯图加特的Wendelin Niedlich画廊举办了联合展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艺术特别展览之一。此次展出的《直线簇II》利用十字线密度的变化产生视觉深度,线条精度达到0.1毫米,成为计算机生成艺术的标志性起点。当这些算法艺术首次出现在传统艺术场所时,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业评论家都受到了极大的困惑和争论。算法革命对艺术产生了几乎未被注意到的影响。
纳克作品《直线簇No.2》资料图
1966年,纳克推出了“Through Grating”系列,利用当时的基本计算机算法语言,将拓扑中的“连接”概念转化为栅格线的参数变化。他在1967年至1968年创作的“矩阵乘法”系列,直接将数学运算转化为视觉符号。计算机自动处理的矩阵乘法的结果成为色彩和形式的来源。1968年,他的作品入选当代艺术研究所的“控制论的意外发现”展览。伦敦和萨格勒布的“Trend 4”展览。1969年,他创作了“生成美学I”系列,从1963年到1969年,他使用的编程算法不断升级,逐渐从机器语言转向PL/I语言(IBM开发的一种多用途编程语言)。
1970年后,纳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数字艺术的理论探索上。在全面总结和提炼实践的基础上他创作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数字艺术,并于1974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信息处理美学》。这部著作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算法艺术”、“生成艺术”、“什么是计算机生成艺术”等学术争议的主要问题,而且系统地发展了以“逻辑-参数变量-视觉输出”为主要结构的算法艺术机制的创作,是第一部数字艺术的方法专着,对建立数字艺术的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计算机艺术的历史地位。
进入21世纪,纳克以“经典作品的当代翻译”为主再次爆发出强烈的热情。 2004年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举办的“精准愉悦”特展中,他在互动投影设备中再现了1966年创作的经典作品《在光栅上行走》。观众的动作可以直接控制动作栏杆的改造,实现了“可视化过程”的当代升级。该设备被卡尔斯鲁厄艺术和媒体中心永久收藏。百年来,他热情拥抱NFT技术,以1960年的经典作品和其他著名画家为原型,创作了《扇面画》(2015)、《直线簇》(2018)、《向格哈德·里希特致敬》(20 18)、《向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致敬》(2018)、《彩色网格》(2025),凯特收藏苏黎世Wass画廊、德国数字艺术博物馆、英国Gazelli艺术博物馆等著名艺术机构。
60多年来,NACK以算法为纽带,将数学、创新技术和艺术自由完美融合,最终成为用代码书写视觉诗歌的数字艺术家。
2 弘扬算法艺术三大审美标志
纳克开创的数字艺术创作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他他们没有用计算机来模仿传统艺术(如油画和素描),而是热衷于获取和探索算法这一新媒介的特征,建立了数字艺术的三个主要审美身份。
一是“算法生成”和“抑制随机性”之美。这是Nak Art的主要特点。他的作品之美并不在于最终的静态图像,而在于孕育图像的“形成过程”。例如,在创作“随机多边形”系列时,他设定了多边形生成的基本规则,同时还引入了随机数来确定多边形的边数、角度和位置。那么,每个任务都是由同一组基因(算法)诞生的独特生命形式,由不同的随机数触发。这种美既不是纯粹的人为安排,也不是绝对的失控意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种受控的、意想不到的绽放之美。oms 在严格的规则框架内。这与传统艺术中依靠艺术家双手的“笔触”和“韵律”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植根于逻辑和可能性的新的审美体验。
二是“系统探索”和“顺序呈现”之美。深受数学思维的影响,纳克的创作很少是单一的“杰作”,而更像是对视觉命题的系统研究。以“矩阵乘法”系列为例,纳克以简单的矩形为基本单位,并通过编程让这些矩形在网格上有规律地旋转。他会为整个系列设定一个规则,然后通过调整参数(例如增加旋转角度),他会生成数十甚至数百件相似但不同的作品,经常并排展示。这种创作方法所带来的美就是顺序和比较。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完美作品而是形式系统内丰富的可能性和进化逻辑。这类美学强调的不是艺术的“独特性”,而是艺术背后“生成系统”的丰富性和严密性。
三是“媒体自显”与“理性朴素”之美。纳克的工作从未试图隐藏这台计算机的起源;相反,他刻意强调并赞扬这种媒介的这些品质。轮廓所描绘出的精确而冷静的线条、有限的色彩(早期多为黑白)、算法生成的人手难以准确再现的复杂几何结构,成为他作品视觉语言的一部分。观看他的画作,比如“线簇”系列中精确的直线图案,观者可以清晰地“读懂”其背后的计算过程和机械执行的痕迹。这类美学不追求情感宣泄,不追求叙事性。叙事,却呈现出一种平静、清晰、高度理性的质朴之美。它引导观众思考艺术品的本质:当艺术家的双手被代码取代时,艺术的灵魂更集中在其立意的严谨与逻辑之美?这种创作理念与传统抽象艺术,如蒙德里安的“构图”有着根本的区别。蒙德里安的几何构图依赖于手工绘制,线条排列的准确性和规律性受到人力的限制。但直线Nack线是由程序控制的,线距误差不超过0.1毫米。这种机械精度是传统手工绘画无法达到的。
通过这三个独特的美学标志,NACK成功地将数字艺术从一种新颖的技术表现形式提升为一种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审美价值的独立艺术形式。正如他所强调的,“算法本身就是艺术,是一种艺术”乌蒂。”
3 定义独特的艺术家主张
纳克的数字艺术作品不仅在美学上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而且在主题表达上也独一无二。其主题之一是“让无形的信息和系统变得可见”。 Nak 本质上是信息结构的视觉翻译器。他热衷于将抽象概念、逻辑关系和数学结构转化为可见的图形,这与传统艺术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情感具体为主要命题,如伦勃朗的《夜巡》传达英雄主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控诉战争的残酷……艺术家利用具体的场景或符号,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可理解的视觉。纳克的作品致力于数学概念的纪念,将微分、概率等抽象的数理逻辑转化为直观的图形语言,让观众欣赏到数学之美无需专业知识。 1965年的《向保罗·克利致敬》就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瑞士著名画家保罗·克利认为“线是行走的点”。他认为线条是独立且富有表现力的元素。线条抽象又具体,能创造出丰富的韵律。 NACK用数学逻辑重构了这个概念,用程序让线条按照预设的概率规则“行走”。作品中,线条的角度角度和延伸长度是在数学约束下由随机函数生成的,既保持了“行走”的自由感,又隐藏了概率分布的数学规律。从线条蜿蜒的轨迹中,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随机中的秩序”这个抽象的数学概念——线条看似随机的运动,实际上每一步都遵循着程序设定的概率模型,实现了精确的配合。数学逻辑和视觉表达之间的联系。这种用图形读懂数学的方式是传统艺术所望尘莫及的。数字技术的可编程性使抽象的公式成为有形的视觉秩序。因此,纳克艺术的主题首先是关于“理解”,关于我们如何以结构化的审美方式来理解世界,以及这种理解如何体现在世界独特的审美形式之间。
纳克作品《向保罗·克利致敬》档案照片
保罗·克利的《红气球》档案照片
纳克艺术作品的另一个艺术哲学命题是规则与偶然性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对主要矛盾:一方面,有预设的、严格的算法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存在着预设的、严格的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随机函数的引入代表着混乱和不确定性。 1965年创作的《随机多边形》是联合国无疑是一部深刻揭示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作品由一条连续的折线组成,NACK在程序中设置了双重逻辑:一方面用严格的代码限制折线的方向范围(仅限水平、特定倾斜角度和偏差方向),生成规则的技术框架;另一方面,引入随机函数来确定顶点坐标,模拟人类创造的自由和灵性。最终的多边形不仅表现出程序提供的规则几何形状,而且由于随机参数而表现出手工创作的独特性。没有两件作品具有完全相同的多边形轨迹。纳克的艺术展现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他通过自己的艺术技巧向世人证明,最具活力的创作往往并非来自于完全的控制或完全的自由,而是诞生于规则与偶然之间的博弈边缘。赛。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为理解自然规律、社会进化乃至人工智能的创造力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此外,纳克的作品还积极触及“人机协同创作”的AI艺术创作主题。在纳克的创作模型中,艺术家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对抗的。艺术家负责定义问题的边界和创作的基本规则(即设计算法),而计算机则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在这个规则空间内进行大规模、高速的探索和生成。人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态度、审美判断和设计规则上,机器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执行力和推理能力上。 1999年NACK主办的“Compart:计算机艺术空间”项目中设计的互动装置就是一个实际例子这个主题。 NACK及其团队开发的参数交互系统允许观看者通过触摸屏调整线条移动的密度、角度和速度,从而实时生成动态图形。当观众在屏幕上滑动改变线变化频率参数时,图像会逐渐从稀疏的线变成密集的视觉矩阵;当调整随机偏差值时,规则的几何数字就会呈现智能变化。这一装置打破了艺术创作者传统的单向输出模式。听众既是创作过程的欣赏者,也是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不同的观众由于习惯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系统同时显示的参数变化让观众直观地了解操作-参数-图形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人机交互和协作的模型明确地预设了这就是6??0年前我们今天在AIGC领域热议的“人机诗人”范式。
4.奠定数字美学的理论基础
NACK不仅是数字艺术的成功实践者,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理论家。他是“信息美学”的主要创始人。该理论试图利用信息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工具对审美现象进行定量和结构化的分析。其领导力表现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纳克的信息美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基本假设——审美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过程。在他看来,算法艺术品就是包含一定“信息结构”的东西。观众欣赏作品的过程就是接受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审美体验或美的强度与审美体验密切相关。作品所传递的信息的结构。借鉴信息论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的信息结构往往处于完全有序(“冗余”太高,导致乏味)和完全无序(“熵”太高,导致误解)之间的最佳平衡。例如,在他的“矩阵乘法”系列作品中,有序网格是高度的“冗余”,提供了顺序;而矩形旋转的随机变化引入了“熵”,带来了新鲜感和动感。两者的平衡有助于提高作品的美感。这一理论尝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视角,可以对高度主观的“美”感进行测试和建模。
其次,这一理论具有浓厚的“反浪漫”色彩,主张基于计算的“理性美学”。这与传统审美形成鲜明对比不要强调天才、灵感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信息美学并不主要关注“艺术表达什么”(内容),而是关注“艺术如何构建其形式”(结构)。它是关于艺术创作作为一种基于逻辑规则的建构活动形式。纳克有时会批评计算机艺术仅被视为技术奇迹的观点。他强调,这个核心的真正价值在于艺术家设计的算法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和逻辑之美。这促使人们思考,艺术的价值是否部分在于其观念的严密性、逻辑的自洽性、生成过程的清晰性。
而且,信息美学体现了数字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过程”本质。对于油画来说,画布上的作品是完成的、封闭的东西。但在Nack的信息美学视野下,alg的真正核心基于算法的艺术是生成作品的“过程”,即算法程序。最终图像只是该过程在某个时刻的示例或输出。这意味着数字艺术品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潜在的系统,包含无限数量的可能的视觉实现。这种“过程胜于结果”的观点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的概念,并直接观察和影响了随后软件艺术、生成艺术、交互艺术的蓬勃发展。
最终,纳克的信息美学理论打破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为数字艺术建立了独立的美学体系。 1960年,当数字艺术首次出现时,艺术界通常使用传统的审美标准,例如形状的均匀性、色彩的和谐性和笔触的活力来评价数字作品。因此,数字艺术一直被认为是边缘艺术。有些人认为机器生成器过时的图形缺乏情感,不被视为艺术,而其他人则将其归类为设计而不是纯粹的艺术。纳克敏锐地意识到数字艺术需要有自己的审美体系,否则就无法摆脱传统艺术的阴影。因此,他从数学和信息论出发,提出以“信息密度”取代传统艺术美学中的“再现的准确性”,作为数字艺术的主要审美标准。他认为数字艺术的本质是基于程序的生成而不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其审美标准应该是“信息密度”,即“作品中包含的重要逻辑信息的组织数量和效率”。这个标准彻底摧毁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他明确指出,数字艺术不需要追求“像传统艺术一样”,其审美价值在于“逻辑信息的丰富性和组织性”。信息”。
从1963年的处女作《随机多边形》到2025年的NFT新作《多彩网格》,纳克始终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不断探索和培育几何之美、生成之美、理性之美的新世界。今天,当我们徜徉在人工智能艺术的奇妙世界,体验“人人都是全能艺术家”的创作乐趣时,我们一定要记住纳克的名言:数字美学的本质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利用新的工具探索人类表达的边界,用逻辑和美来传达对世界的思考。数字艺术的未来不在于技术能走多远,而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技术来表达对人类、对生命、对世界的关注。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0日第13页)
作者:焦亚男(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数字艺术从以计算机生成艺术为标志的第一代、以数字奇迹为标志的第二代、以互动艺术为标志的第三代,迭代发展到目前以人工智能艺术为标志的第四代。当我们陶醉在四代数字艺术构建的万花筒般的美学景观中时,我们不能忘记炸nack,数字艺术的火种。作为最早将数学逻辑、计算机编程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先驱者,纳克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不仅奠定了数字艺术的早期形态,也建立了数字美学大厦的基本框架。为了表彰他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国际计算机图形学信用联盟授予他“2025 Dig意大利艺术终身成就奖。”
纳克作品《生成美学i》资料图
1 成为一名跨界艺术家
纳克1938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60年在斯图加特大学学习数学,1963年在斯图加特大学计算中心实习,协助负责“程序库”的老师。他的工作性质就像助教,又有点像软件开发人员。一天早上,计算中心主任沃尔特·诺德尔告诉他,计算中心打算购买一台绘图机,但没有合适的软件,并要求纳克编写一个绘图程序。 Knodel 教授的 T 给了 rustful 委员会一个机会,为新型自动平板绘图仪 Z64 开发软件程序。正是从此开始的编程实验,开始了纳克一生中数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探索阶段。
油炸纳克文件照片
一个这一阶段,纳克的创作以“绘图仪几何美学”为中心。 1963年至1965年,他使用ER56计算机和Z64高精度绘图仪创作了“随机多边形”系列、“线簇II”系列、“随机遍历”系列和“向保罗·克利致敬”系列。 1965年11月,他与乔治·内斯在斯图加特的Wendelin Niedlich画廊举办了联合展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艺术特别展览之一。此次展出的《直线簇II》利用十字线密度的变化产生视觉深度,线条精度达到0.1毫米,成为计算机生成艺术的标志性起点。当这些算法艺术首次出现在传统艺术场所时,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业评论家都受到了极大的困惑和争论。算法革命对艺术产生了几乎未被注意到的影响。
纳克作品《直线簇No.2》资料图
1966年,纳克推出了“Through Grating”系列,利用当时的基本计算机算法语言,将拓扑中的“连接”概念转化为栅格线的参数变化。他在1967年至1968年创作的“矩阵乘法”系列,直接将数学运算转化为视觉符号。计算机自动处理的矩阵乘法的结果成为色彩和形式的来源。1968年,他的作品入选当代艺术研究所的“控制论的意外发现”展览。伦敦和萨格勒布的“Trend 4”展览。1969年,他创作了“生成美学I”系列,从1963年到1969年,他使用的编程算法不断升级,逐渐从机器语言转向PL/I语言(IBM开发的一种多用途编程语言)。
1970年后,纳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数字艺术的理论探索上。在全面总结和提炼实践的基础上他创作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数字艺术,并于1974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信息处理美学》。这部著作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算法艺术”、“生成艺术”、“什么是计算机生成艺术”等学术争议的主要问题,而且系统地发展了以“逻辑-参数变量-视觉输出”为主要结构的算法艺术机制的创作,是第一部数字艺术的方法专着,对建立数字艺术的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计算机艺术的历史地位。
进入21世纪,纳克以“经典作品的当代翻译”为主再次爆发出强烈的热情。 2004年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举办的“精准愉悦”特展中,他在互动投影设备中再现了1966年创作的经典作品《在光栅上行走》。观众的动作可以直接控制动作栏杆的改造,实现了“可视化过程”的当代升级。该设备被卡尔斯鲁厄艺术和媒体中心永久收藏。百年来,他热情拥抱NFT技术,以1960年的经典作品和其他著名画家为原型,创作了《扇面画》(2015)、《直线簇》(2018)、《向格哈德·里希特致敬》(20 18)、《向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致敬》(2018)、《彩色网格》(2025),凯特收藏苏黎世Wass画廊、德国数字艺术博物馆、英国Gazelli艺术博物馆等著名艺术机构。
60多年来,NACK以算法为纽带,将数学、创新技术和艺术自由完美融合,最终成为用代码书写视觉诗歌的数字艺术家。
2 弘扬算法艺术三大审美标志
纳克开创的数字艺术创作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他他们没有用计算机来模仿传统艺术(如油画和素描),而是热衷于获取和探索算法这一新媒介的特征,建立了数字艺术的三个主要审美身份。
一是“算法生成”和“抑制随机性”之美。这是Nak Art的主要特点。他的作品之美并不在于最终的静态图像,而在于孕育图像的“形成过程”。例如,在创作“随机多边形”系列时,他设定了多边形生成的基本规则,同时还引入了随机数来确定多边形的边数、角度和位置。那么,每个任务都是由同一组基因(算法)诞生的独特生命形式,由不同的随机数触发。这种美既不是纯粹的人为安排,也不是绝对的失控意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种受控的、意想不到的绽放之美。oms 在严格的规则框架内。这与传统艺术中依靠艺术家双手的“笔触”和“韵律”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植根于逻辑和可能性的新的审美体验。
二是“系统探索”和“顺序呈现”之美。深受数学思维的影响,纳克的创作很少是单一的“杰作”,而更像是对视觉命题的系统研究。以“矩阵乘法”系列为例,纳克以简单的矩形为基本单位,并通过编程让这些矩形在网格上有规律地旋转。他会为整个系列设定一个规则,然后通过调整参数(例如增加旋转角度),他会生成数十甚至数百件相似但不同的作品,经常并排展示。这种创作方法所带来的美就是顺序和比较。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完美作品而是形式系统内丰富的可能性和进化逻辑。这类美学强调的不是艺术的“独特性”,而是艺术背后“生成系统”的丰富性和严密性。
三是“媒体自显”与“理性朴素”之美。纳克的工作从未试图隐藏这台计算机的起源;相反,他刻意强调并赞扬这种媒介的这些品质。轮廓所描绘出的精确而冷静的线条、有限的色彩(早期多为黑白)、算法生成的人手难以准确再现的复杂几何结构,成为他作品视觉语言的一部分。观看他的画作,比如“线簇”系列中精确的直线图案,观者可以清晰地“读懂”其背后的计算过程和机械执行的痕迹。这类美学不追求情感宣泄,不追求叙事性。叙事,却呈现出一种平静、清晰、高度理性的质朴之美。它引导观众思考艺术品的本质:当艺术家的双手被代码取代时,艺术的灵魂更集中在其立意的严谨与逻辑之美?这种创作理念与传统抽象艺术,如蒙德里安的“构图”有着根本的区别。蒙德里安的几何构图依赖于手工绘制,线条排列的准确性和规律性受到人力的限制。但直线Nack线是由程序控制的,线距误差不超过0.1毫米。这种机械精度是传统手工绘画无法达到的。
通过这三个独特的美学标志,NACK成功地将数字艺术从一种新颖的技术表现形式提升为一种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审美价值的独立艺术形式。正如他所强调的,“算法本身就是艺术,是一种艺术”乌蒂。”
3 定义独特的艺术家主张
纳克的数字艺术作品不仅在美学上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而且在主题表达上也独一无二。其主题之一是“让无形的信息和系统变得可见”。 Nak 本质上是信息结构的视觉翻译器。他热衷于将抽象概念、逻辑关系和数学结构转化为可见的图形,这与传统艺术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情感具体为主要命题,如伦勃朗的《夜巡》传达英雄主义,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控诉战争的残酷……艺术家利用具体的场景或符号,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可理解的视觉。纳克的作品致力于数学概念的纪念,将微分、概率等抽象的数理逻辑转化为直观的图形语言,让观众欣赏到数学之美无需专业知识。 1965年的《向保罗·克利致敬》就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瑞士著名画家保罗·克利认为“线是行走的点”。他认为线条是独立且富有表现力的元素。线条抽象又具体,能创造出丰富的韵律。 NACK用数学逻辑重构了这个概念,用程序让线条按照预设的概率规则“行走”。作品中,线条的角度角度和延伸长度是在数学约束下由随机函数生成的,既保持了“行走”的自由感,又隐藏了概率分布的数学规律。从线条蜿蜒的轨迹中,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随机中的秩序”这个抽象的数学概念——线条看似随机的运动,实际上每一步都遵循着程序设定的概率模型,实现了精确的配合。数学逻辑和视觉表达之间的联系。这种用图形读懂数学的方式是传统艺术所望尘莫及的。数字技术的可编程性使抽象的公式成为有形的视觉秩序。因此,纳克艺术的主题首先是关于“理解”,关于我们如何以结构化的审美方式来理解世界,以及这种理解如何体现在世界独特的审美形式之间。
纳克作品《向保罗·克利致敬》档案照片
保罗·克利的《红气球》档案照片
纳克艺术作品的另一个艺术哲学命题是规则与偶然性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对主要矛盾:一方面,有预设的、严格的算法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存在着预设的、严格的算法,代表着秩序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随机函数的引入代表着混乱和不确定性。 1965年创作的《随机多边形》是联合国无疑是一部深刻揭示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作品由一条连续的折线组成,NACK在程序中设置了双重逻辑:一方面用严格的代码限制折线的方向范围(仅限水平、特定倾斜角度和偏差方向),生成规则的技术框架;另一方面,引入随机函数来确定顶点坐标,模拟人类创造的自由和灵性。最终的多边形不仅表现出程序提供的规则几何形状,而且由于随机参数而表现出手工创作的独特性。没有两件作品具有完全相同的多边形轨迹。纳克的艺术展现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他通过自己的艺术技巧向世人证明,最具活力的创作往往并非来自于完全的控制或完全的自由,而是诞生于规则与偶然之间的博弈边缘。赛。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为理解自然规律、社会进化乃至人工智能的创造力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此外,纳克的作品还积极触及“人机协同创作”的AI艺术创作主题。在纳克的创作模型中,艺术家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对抗的。艺术家负责定义问题的边界和创作的基本规则(即设计算法),而计算机则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在这个规则空间内进行大规模、高速的探索和生成。人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态度、审美判断和设计规则上,机器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执行力和推理能力上。 1999年NACK主办的“Compart:计算机艺术空间”项目中设计的互动装置就是一个实际例子这个主题。 NACK及其团队开发的参数交互系统允许观看者通过触摸屏调整线条移动的密度、角度和速度,从而实时生成动态图形。当观众在屏幕上滑动改变线变化频率参数时,图像会逐渐从稀疏的线变成密集的视觉矩阵;当调整随机偏差值时,规则的几何数字就会呈现智能变化。这一装置打破了艺术创作者传统的单向输出模式。听众既是创作过程的欣赏者,也是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不同的观众由于习惯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系统同时显示的参数变化让观众直观地了解操作-参数-图形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人机交互和协作的模型明确地预设了这就是6??0年前我们今天在AIGC领域热议的“人机诗人”范式。
4.奠定数字美学的理论基础
NACK不仅是数字艺术的成功实践者,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理论家。他是“信息美学”的主要创始人。该理论试图利用信息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工具对审美现象进行定量和结构化的分析。其领导力表现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纳克的信息美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基本假设——审美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加工过程。在他看来,算法艺术品就是包含一定“信息结构”的东西。观众欣赏作品的过程就是接受和处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审美体验或美的强度与审美体验密切相关。作品所传递的信息的结构。借鉴信息论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的信息结构往往处于完全有序(“冗余”太高,导致乏味)和完全无序(“熵”太高,导致误解)之间的最佳平衡。例如,在他的“矩阵乘法”系列作品中,有序网格是高度的“冗余”,提供了顺序;而矩形旋转的随机变化引入了“熵”,带来了新鲜感和动感。两者的平衡有助于提高作品的美感。这一理论尝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视角,可以对高度主观的“美”感进行测试和建模。
其次,这一理论具有浓厚的“反浪漫”色彩,主张基于计算的“理性美学”。这与传统审美形成鲜明对比不要强调天才、灵感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信息美学并不主要关注“艺术表达什么”(内容),而是关注“艺术如何构建其形式”(结构)。它是关于艺术创作作为一种基于逻辑规则的建构活动形式。纳克有时会批评计算机艺术仅被视为技术奇迹的观点。他强调,这个核心的真正价值在于艺术家设计的算法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和逻辑之美。这促使人们思考,艺术的价值是否部分在于其观念的严密性、逻辑的自洽性、生成过程的清晰性。
而且,信息美学体现了数字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过程”本质。对于油画来说,画布上的作品是完成的、封闭的东西。但在Nack的信息美学视野下,alg的真正核心基于算法的艺术是生成作品的“过程”,即算法程序。最终图像只是该过程在某个时刻的示例或输出。这意味着数字艺术品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潜在的系统,包含无限数量的可能的视觉实现。这种“过程胜于结果”的观点极大地拓展了艺术的概念,并直接观察和影响了随后软件艺术、生成艺术、交互艺术的蓬勃发展。
最终,纳克的信息美学理论打破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为数字艺术建立了独立的美学体系。 1960年,当数字艺术首次出现时,艺术界通常使用传统的审美标准,例如形状的均匀性、色彩的和谐性和笔触的活力来评价数字作品。因此,数字艺术一直被认为是边缘艺术。有些人认为机器生成器过时的图形缺乏情感,不被视为艺术,而其他人则将其归类为设计而不是纯粹的艺术。纳克敏锐地意识到数字艺术需要有自己的审美体系,否则就无法摆脱传统艺术的阴影。因此,他从数学和信息论出发,提出以“信息密度”取代传统艺术美学中的“再现的准确性”,作为数字艺术的主要审美标准。他认为数字艺术的本质是基于程序的生成而不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其审美标准应该是“信息密度”,即“作品中包含的重要逻辑信息的组织数量和效率”。这个标准彻底摧毁了传统美学的霸权。他明确指出,数字艺术不需要追求“像传统艺术一样”,其审美价值在于“逻辑信息的丰富性和组织性”。信息”。
从1963年的处女作《随机多边形》到2025年的NFT新作《多彩网格》,纳克始终站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不断探索和培育几何之美、生成之美、理性之美的新世界。今天,当我们徜徉在人工智能艺术的奇妙世界,体验“人人都是全能艺术家”的创作乐趣时,我们一定要记住纳克的名言:数字美学的本质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利用新的工具探索人类表达的边界,用逻辑和美来传达对世界的思考。数字艺术的未来不在于技术能走多远,而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技术来表达对人类、对生命、对世界的关注。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0日第13页)

